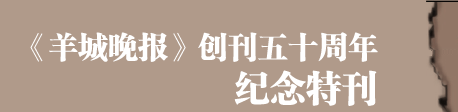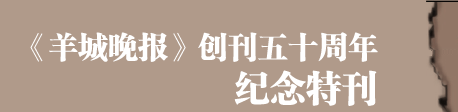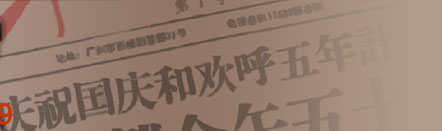这是一个沉于思,而默于言的时代。从1966年12月到1980年2月,《羊城晚报》被迫停刊13年零两个月。
俗语道:性格即命运。与生俱来的“另辟蹊径”,注定《羊城晚报》命中有此大劫。
报界有个专用名词 ——“开天窗”,意思是版面上出现了由于非正常抽稿导致的非正常空白。
因为发表“大毒草”,《羊城晚报》整张报纸被“抽”,它历史的版面开了“天窗”。导火索是一篇散文 ——《韶山的节日》。作家周立波的“错”——把领袖还原成人,而非神。《羊城晚报》的“错”,在“造神”大潮中逆流而上,天真地以为删除一些细节就没事了,诸如领袖在父母坟前跪拜之类。
当时的时代背景是,“极左”之风愈演愈烈,并且迅速演变成了猛烈的政治风暴。文化领域首当其冲,那就是被今天的“80后”视为“发生在古代”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前辈的回忆并不见得悲壮——停刊后,全体采编人员都到五七干校劳动: 《艺海拾贝》的作者秦牧成了一把劳动好手;老编老记们最感自豪的一件事情是,知青们把他们带去垫床板的旧《羊城晚报》当成了宝贝;他们对轮流当伙夫的经历也印象深刻,得意于学会了用大铁锅煮饭……他们从不自怨自艾,从容接受苦难,从未泯灭理想。
或许,这正是未来若干年以后,一旦出幽谷迁于乔木,他们就能以木秀于林的姿态爆发出巨大能量的原因吧。
可以这样认为:《羊城晚报》历史上有一个“天窗”,而羊城晚报人的精神上从未存在过“天窗”。 |